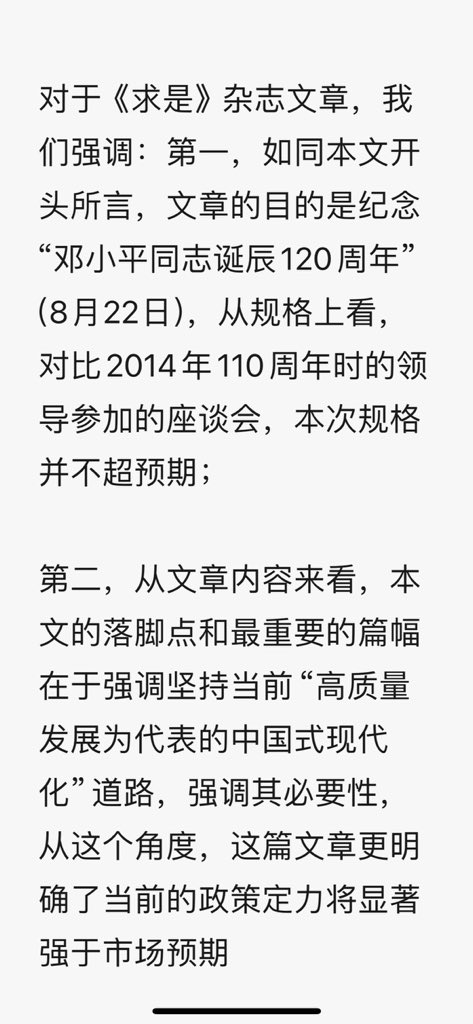倒不是非要全职交易,看交易和打工的效率,也不排除动态切换。至少尽量不做长期的全职工作,那会限制肉身,某些情况下可能要不得不而不是主动去做数字游民,那收入就必须能够从网络获取。
#### 哈里斯的经济纲领:教科书式的完美错误!
原创 风灵之声 风灵 2024年08月19日
文 风灵
美国民主党新晋总统候选人哈里斯近日推出了她的经济政策竞选纲领。就美国人最关心的通货膨胀问题,哈里斯保证,如果她上台,一百天内就可以控制通货膨胀,主要举措包括:
一是各种补贴。其中包括给予抚育儿童的家庭3600-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大约要1.2万亿美元预算);购房补贴,首次购房发2.5万美元补贴;医疗债务减免和药费每年2000美元封顶,也是政府帮你买单;低收入税收抵免,每年最多可多得1500美元。
二是价格管制,严厉打击哄抬物价的“价格欺诈”行为。
光天化日之下,哈里斯竟然明目张胆地抛出了这样一套犯下了教科书式完美错误的经济纲领,真是认为美国人好哄骗吗?
任何人,只要学过一丁点经济学常识都应该知道,如果一个国家面临通货膨胀,那最不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首先不该做的当然就是发钱印钞;其次是价格管制。而哈里斯恰恰精准无误地踏入了这两大禁区!
不需要很高深的道理。通货膨胀之所以发生,就是货币泛滥,这次美国大通胀主要就是疫情期间大撒币发钱,同时又减少了生产性活动而造成的。现在,哈里斯面对民众的抱怨,为了拉选票承诺再次大把发钱,以解决生活困难。但钱从哪里来?哈里斯既然也承诺了减税(加税当然也不行),资金来源无非是借债印钞,即政府为弥补赤字发行国债,然后美联储购买国债,就是以凭空创造的新货币来支付。这无疑于负薪救火,火上浇油,将进一步推高物价。于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漩涡就将在眼前形成了!
经济学大师米塞斯曾反复告诫过这种情况:“政府需要解决赤字问题,而税收又不足弥补赤字,于是就在无抵押品的情况下发行货币,陷入螺旋式通货膨胀。如果持续下去,将形成灾难性的漩涡。”
殷鉴真真实实地不远,就在称为美国后院的拉美,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就曾长期卷入恶性通货膨胀螺旋。委内瑞拉通胀最严重的时候,钞票连字面意义上的手纸都不如。人们宁可直接用钞票当手纸,而不是花钱去买。而历史上恶性通货膨胀的翘楚,德国魏玛共和国,到1923年11月,1美元兑换约4.2万亿马克,相较一战之前1914年1美元兑换4.2马克,足足膨胀了1万亿倍!无数人积攒一生的财富都在恶性通货膨胀中化为乌有,正常经济活动难以进行,人们只能转向以物易物的交易,投资、信贷等当然更无从谈起。
自拜登政府2021年1月上任以来,美国的国债增加了约 $6.4 至 $7.3万亿,国债总额从$27.8万亿飙升至目前超过$35万亿。2024年,美国国债的利息占联邦政府收入的比重将超过20%。如果哈里斯的经济政策真的得以实施,美国的财政收支状况显然会更为急剧恶化。以前我们说,美国有可能变成委内瑞拉,那还只是担忧的话,现在,哈里斯已经清楚无误地指明了“通往委内瑞拉之路”。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哈里斯还要管制零售价格。不要去听什么“价格欺诈”的说辞,制造出通货膨胀的政府不可能下罪己诏,最好的背锅侠当然就是“哄抬物价的奸商”。
价格管制,或者照哈里斯的说法“打击价格欺诈”,就是迫使(至少某些)商家以不盈利的方式销售,那显然会减少供给,制造短缺。而但凡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经营过的人,哪怕只是摆过地摊或开过网店,也都知道,商家能不能“哄抬物价”,能不能想怎么定价就怎么定价。
米塞斯也曾以牛奶为例,阐述过价格管制的危害。
“政府听到人们抱怨,牛奶的价格上涨了。牛奶当然非常重要,因此,政府宣布了牛奶的最高限价,比可能的市场价格更低的最高限价。一方面,较低的牛奶价格增加了对牛奶的需求。另一方面,某些生产商,即那些成本最高的牛奶生产商,也就是边际生产者,遭受亏损。因此,政府对牛奶价格的干预导致了牛奶的供给减少,同时需求却增加。在政府干预牛奶之前,牛奶价格虽高,但人们买得到。而现在,人们能买到的牛奶却更少了。”
现实当中,委内瑞拉在通货膨胀的时候管制价格,企业一圈圈地依次倒闭或者停业,百业凋敝。不信邪的政府国有化接管“不听话”的企业,面对成本和管制价格的倒挂,政府也只能加印钞票“补贴”,其结果当然是更加疯狂的通胀螺旋!
再接下来,政府如果一定要把通胀的“数据”降下来,可能会在普遍管制造成供给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实行配给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其实与拜登政府一脉相承,只是更左更激进更放飞自我。正是拜登政府一手造成了现在的通货膨胀,而哈里斯还要继续一条道走到黑。今年11月如果真的是哈里斯上台,那大家就自求多福吧!如果美国爆发本国历史上未见的恶性通货膨胀灾难,其后果当然不是美国一国遭殃,世界经济将受到多大的冲击,难以想象。(本文不打算评论川普的经济政策,不过川普至少没有这么夸张的教科书式错误。)
那应该怎样应对通货膨胀呢?阿根廷的米莱总统正在示范。首先当然就是要严格财政纪律,严禁再滥发货币,尽一切可能缩减政府开支;同时,放开物价管制,放开进出口管制和其他各种经济管制。简言之,商品和货币可看作是天平的两端,如果已经失衡了,正确的做法是减少货币供给的同时增加商品供给,而不是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减少商品供给。米莱的措施已初见成效,2024年7月,阿根廷当月通胀率为4%,只有2023年12月12.4%的通胀率不到三分之一。
哈里斯这份发钱+管制的政纲,明显是为了迎合某些头脑简单的左派选民,由此可见美国的教育有了严重问题。同时,我也看到国内有不少人叫好,这表明经济学常识的普及确实还任重道远。
缺钱就印钱发钱,买不起东西就免费提供,价格高了就打击奸商,如果这样直截了当就能奏效的话,人间天堂早就实现了。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识别谬误,因此,我真诚希望每个人都读一读米塞斯的《六堂课:经济政策》,以免被糖衣炮弹所惑,赞同、支持甚至呼吁错误的经济政策,为灾难推波助澜而不自知。参见:如果你关心你的国家,去读米塞斯的六堂课!
智识的积累就像资本的积累,好的投资有看起来拉长生产结构,花费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成本在表面不太相关的事物,迂回生产只要能找到极大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最终会像最速降线一样,行程大于直线却能更早到达。
艺术源于生活,小说或剧本作者要做的,就是删除现实生活中冗长无聊的部分,以前还想孙红雷姚晨离婚那个桥段编的离谱😅
#### 法国大革命期间的通货膨胀、价格控制和集体主义
文:理查德·埃贝林 (Richard M.Ebeling)
编译:禅⼼云起 编辑:瑞秋的春天
各国政府贪图其臣民财富,正可谓欲壑难填。当政府发现无法继续增加税收或贷款时,它们总是转而印刷纸币,以求为其不断扩张的支出提供资金。由此产生的通货膨胀,往往破坏社会结构、摧毁经济,并时常以革命和暴政收尾。
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就是一个悲剧性的例子。在1789年革命之前,君主制法国是重商主义的教材范例。如果没有政府的批准和管制,就既不能生产,也不能买卖,就既不能进口,也不能出口。
政府奢侈和财政浪费
当法国君主政府管理经济事务时,王室消耗着全体国民的财富。光路易十六的个人卫队就达9,050人;宫廷里大约有4,000人——30名仆人服伺国王进餐,其中4人的使命是为他的酒杯斟上酒水。他还享有128名乐师、75名神职人员、48名医生的伺候,198人负责照料他的身体。
为满足这样的穷奢极欲及支付王室的其他许多费用,以及资助的国外冒险(比如在北美从英国独立的战争期间,向北美殖民地人民提供的财政援助),法王必须依赖于一个特殊的税收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全体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主要是贵族、僧侣——豁免所有税收,而“较低等级”承担主要的重负。
最遭人痛恨的税收之一是盐税。每一家户主每年都需要按照政府规定的盐价,替家庭成员每人购买七磅食盐;如果上年存货没吃完,本年购买数量要想少于摊派的份额,他就会遭到这个国家的特别罚款。对走私食盐和黑市贩卖私盐的惩罚都是惨无人道的。
正如我们先前文章所看到的,当路易十六在1774年继任王位时,政府支出为3.992亿卢比,税收仅约3.72亿里弗,赤字有2720万卢比,约占支出的7%。当年和未来几年的借贷和货币扩张弥补了亏欠。
为打理政府财政,1774年7月,法王任命了一位杰出经济学家——安·罗伯特·雅克·杜尔阁——担任财政部长。杜尔哥竭力遏制政府支出和管制。但是他提议的每项改革,都遭到特权集团愈来愈强烈的反对。1776年5月,法王最终让他卸任。
那些接替杜尔哥特担任法国政府财政总监的人,既没有他的视野,也缺少他的诚信。财政危机一味恶化。正如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在他《法国大革命》(1837)的研究中所概括的,
“无论是‘缺少财务天才’,还是缺乏别的什么,收不抵支的差距极其显著,财政赤字(…)造成了一个严峻问题:就像化方为圆一般令人绝望。财务总监若利・德・弗勒里,雅克·内克的继任者,根本束手无策,除了借钱来一点点填补窟窿的建议;征收新税,不仅榨不出钱,反而带来舆论的喧嚣和不满。
总监朵尔梅松能做的甚至更加可怜;如果说若利尚能撑满一年,朵尔梅松只能撑几个月(…)
致命的瘫痪侵入社会活动;到处密云笼罩、暗无天日,我们正陷入国家破产的不祥恐怖?”
正是法王财政的混乱,最终导致三级会议在1789年初的召集,之后是1789年7月巴黎巴士底狱沦陷,法国大革命开端。然而,新的革命政府,也像国王一样奢侈花费,为创造就业机会,把大量资金花在公共工程。巴黎人得到的粮食补贴,就达1700万英镑(340万美元)。
“指券”:纸币
和疯狂的物价上涨
1789年11月,奥诺莱·米拉波给出了解决一切政府财政困难的答案。上个月,国民议会刚把教会的所有土地及资产国有化。米拉波建议国民议会以教会土地作抵押来发行纸钞。钞票首先作为公共工程的开支和政府的其他费用进入流通。它们将按面值以教会财产售价的形式赎回。
与此同时,有人认为,增加的货币流通会给产业带来“刺激”,创造就业机会,从而把钱装入劳动阶级的口袋里。(后来,逃离贵族的没收土地,被充作支撑泛滥纸币假想的抵押品。)
1790年3月17日,革命国民议会投票发行一种名为“指券”的新纸币,4月份,4亿指券(8,000万美元)投入发行。由于缺乏资金,政府在夏季结束时再发行了8亿指券(1.6亿美元)。西摩·哈里斯在他《指券》(1930)一书的研究当中,描绘了纸币的一路贬值。1791年底,有18亿指券处于流通中,其购买力下降14%。1793年8月,指券数量增至近49亿,贬值60%。1795年11月,指券达197亿。这时,其购买力自第一次发行后下降了99%。五年来,革命法国的纸钞甚至变得比印刷它所用的纸还要不值钱。
这种货币崩溃的影响极为惊人。一个庞大的债务阶级,由通货膨胀的既得利益所创造,因为贬值的指券,意味着债务人能用越来越没有价值的钱来清偿债务。其他人投机土地,通常是政府扣押和卖掉的前教会财产。他们的财富现在与土地价值的不断上涨息息相关。随着钱一天天不值钱,片刻欢娱远胜过长期规划投资。
货物被囤积,因此变得稀罕——因为卖家预料物价高涨,将一日更甚一日。肥皂变得如此稀缺,于是巴黎的洗衣妇们呼吁:那些拒绝向她们售予商品并接受指券的卖家,统统应被处死。1793年2月,巴黎暴民袭击了200多家商店,抢走了从面包、咖啡、糖到服装等等一切东西。
亨利克·冯·塞贝尔(1817-1895),在他四卷《法国大革命史》(1867年)中,解释了当时的社会和心理环境:
“没有人对未来抱有信心;很少有人敢在任何时候进行任何商业投资,这被认为是减少了眼前欢乐以图一个看不到的未来,或为这样的未来积蓄的愚蠢之举(…)
谁拥有少量指币或银币,都趁早把它们花在尽情享受,渴望抓住每个稍纵即逝的享乐刺激。入秋,所有剧院重新开放,人们热情不竭、不知疲倦(…)歌剧院和咖啡馆的喧闹,丝毫不逊于剧院。城市的每个街区,夜夜歌舞升平(…)
这些享受,也从革命的回忆和感受中获得了奇特色彩——耀眼的光芒和黯淡的阴影(…)在有的交际圈内,哪个人如果没有亲人在断头台上丧命,就得不到接纳;时尚舞会服装,模仿那些被带往刑场者的短发和翻领;绅士们对舞伴作出一个特别的点头示意,旨在提醒大家断头落地。”
通胀负担主要落在谁的身上?最贫穷潦倒的人。参与国际贸易的金融家、商人和商品投机者,通常可以保护自己。他们积蓄了金银,送到国外保管;他们还投资艺术品和珍贵的首饰。他们的投机专长,使他们许多人始终能够领先于通胀,并从货币价格波动中获利。劳动阶级和穷人,一般都没有专门知识和手段来保护他们的微薄身家。他们是最终拥有那数十亿指券废纸的人。
最后,1795年12月22日,政府命令停止指券印刷。遭到禁止的金银交易再度得到许可,重获法律约束力。1796年2月18日早上9点,用于制作指券的印刷机、印版和纸张被送到旺多姆广场,在巴黎群众面前被砸碎和焚毁。
试图抵御通胀的
灾难性价格控制
然而,在“指券”谢幕前,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人民”的怒吼震耳欲聋,必须阻止价格上涨。1793年5月4日,国民议会对粮食实行价格管制,并规定只能在国家督查员的监视下,才能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粮食。他们也有权闯进商人的私人住宅,没收囤积的粮食和面粉。根据政府规定,销毁这种货物是一项死罪。
1793年9月,价格控制扩展到所有被宣称为“基本必需品”的货物。1790年,严禁物价涨幅超过三分之一。1794年春,工资被置于类似的控制线下。尽管如此,商品很快从市场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巴黎各家咖啡馆发现无法获得糖;粮食供应减少,因为农民拒绝将他们的农产品运往城市。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温·甘末尔(1875-1945)在其著作《货币》(1935)一书对法国大革命经济的研究中,解释了规避价格控制的一些方法,
“在规避这种固定价格制度所用的方法中,可以举出以下几种:从市场撤走货物,以及在现有库存用尽时,不再生产新的货物;在产出和销售中以次充好;当小麦有最高限价而活牲没有限价时,就用小麦喂养地里的牲畜;当小麦价格受到控制而面粉价格不受控制时,农民就把小麦磨成面粉。
农民在家里秘密出售他们的农产品,而不是销往市场。当原材料价格受到控制时,制成品价格就会频繁而异常地上涨,当生活必需品价格被压低时,奢侈品价格就会迅速飙升。
规避管制法令的人,一旦就擒,所受惩罚极其残酷,巨大利润由此而生。这导致了大量官员腐败。以管制价格在市场上获得的货物供应一向不足,而排队成为一种制度惯例,就像今天的苏俄城市。”
凌驾个人之上
的全权国家意识形态
在1792-1794年的雅各宾共和国,一大批监管机构遍布法国。它们设立价格上限,侵入人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们执行死刑,没收财富和财产,将男人、女人、儿童押往监狱,送去从事奴役劳动。在革命法国与许多邻国发生冲突后,所有与国防或外贸有关的行业,都以战争名义被国家直接控制;价格、生产和所有商品分配皆由政府指挥。一个管理一切的庞大官僚机构出现,而官僚主义吞噬了愈来愈多的国民财富。
这一切都自然源于雅各宾思想的前提,即在卢梭式“公意”概念的阴影下,认为国家有责任强加给每个人一个共同目的。个人什么都不是。国家才是一切。个人变得面目抽象,而国家才是现实。那些不晓得“公意”的人,就会受到教导;那些违抗教导的人,就会得到命令;那些违抗命令的人,就会走向灭亡。因为只有“人民公敌”才会反对这个集体主义的真理。
法国革命家伯特兰·巴雷尔(1755-1841)在1793年宣布,
“共和国必须从每个感官渗入公民的灵魂(…)(对于法国)有些人欠下了自己的劳动,有些人欠下了自己的财富,有些人欠下了自己的忠告,还有些人欠下了自己的臂膀;全体人都向她欠下了自己的鲜血。因此,所有法国人,无论性别或年龄,都要受到爱国主义的感召,起来保卫自由(…)
让人人都在预备当中的国家和军事行动中服役。青年战斗在一线;已婚男子制造武器,运输辎重军需,提供补给;妇女制作军衣、缝制帐篷,化身为照料伤员的医院护士;孩子们从亚麻布中抽出引绳(注:火枪用的火绳);而老人再次执行古老的使命,他们被带往公共广场,鼓舞年轻战士的勇气,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
所有法律、风俗、习惯、商业模式、思想和语言都是统一的,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模一样。家庭不复自主存在;至于儿童?他们属于国家。巴雷尔说:
“应该指导父母的原则是,在属于特定家庭之前,儿童属于共和国的公共家庭。当大家庭召唤时,私人生活的气氛必须消失。你是为了共和国,而不是为了家庭的傲慢和专制而生。”
这就是现代国民集体主义和对“人民”国家效忠服从的诞生。1793年1月,一位信使被派去法国革命军队,通知法王被处决的消息。法军正在法国东部与反革命外国君主的入侵军队对峙。这时,一名法国军官问:“从现在开始,我们要为谁而战呢,”如果不是国王?答复是:“为了国民、为了共和国。”
回归自由市场的原则
1794年底,反雅各宾的热月党人控制了政府,一批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其中一位埃沙塞里奥宣称:“当农民、制造商和贸易商都享有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产和自己的劳动的充分自由(…)这样的经济制度才是一个好的制度。”
他的同事蒂博多主张:“我认为最高限价是灾难性的,是我们经历的所有不幸的根源。它为盗贼创造了职业,让走私在法国泛滥,毁掉了尊重法律的诚实人(…)我清楚,当政府试图管理一切时,一切都无可救药了。”
最后,1794年12月27日,价格和工资控制被取消,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条件再度得到允许。在指券终结一年后,货物再次流入市场,繁荣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正如阿道夫·蒂尔斯(1797-1877)在他的《法国大革命史》(1842)一书中所描述的,
“没人再使用白银以外的东西交易。先前显然被隐匿或输出国外的这些货币,重新占据了流通——被藏起来的,重见天日,被携离法国的,又被带回来了(…)
黄金和白银,像所有商品一样,流动到需求吸引它们的地方,金银的价格升高,直到供应充足、需求满足,就维持在某个水平。金银一旦出现在市场上,人们的工资也以同样方式支付。
人们当时也许会说,法国再不会有纸币。权证(指券)只有在投机者手中才能找到,他们从政府那里接收这些权证,并转售给国家资产的买家。因此,金融危机对国家来说仍然存在,但对于个人来说,则几乎不复存在。”
法国大革命期间经历的集体主义思想和经济政策类型,在更晚近的现代,仍然反复登场,依旧不乏支持,举例而言,体现在包括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著名经济学家的作品当中。
1936年底,奥地利出生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对凯恩斯最新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写了一篇评论。这部著作,在短短几年间,就成为凯恩斯主义“新经济学”的圣经。熊彼特凭观察得出结论说,
“接受(凯恩斯在《通论》当中所阐明的)这些信息的人,就用以下措辞改写法国旧制度(政权)的历史吧:
路易十六乃一位贤明君主。他认识到刺激支出的必要性,并获得了像名媛德·蓬帕杜夫人和德·巴里夫人这样消费专家的协助。她们以卓越无比的效率工作。结果本应是充分就业、产出和总福利的最大化。惨不可言、血流成河的相反结局,诚然尽人皆知,但也不过是一个偶然巧合罢了。”
这些是名义上的税,还有字面不带“税”的税,比如社保税由社畜和企业按约1:3比例分摊,还有无形却数额巨大的通胀税。
政府的横征暴敛,除税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非税”,如行政罚款及各种摊派费用等等。
#### 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重大失误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普鲁士议会下院(Abgeordnetenhaus)以普选权为基础。每个选区的公民被分为三类,每类公民选出同样数量的选举人,由选举人进行最后投票,选出该选区的议会代表。第一类公民,由适用税率最高,且合计纳税额达到本区前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居民组成;合计纳税额达到第二个三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居民为第二类;合计纳税额为第三个三分之一成年男性居民为第三类。因此,较富有的公民比同选区内较贫穷的公民,享有更多的选举权重。中产阶级在选票中占优。但是,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和后来的德意志帝国议会则没有这种区别对待。每个成年男性直接投票选出本选区议会代表,选举权不仅普遍而且平等和直接。因此,较贫穷的阶层获得了更多的政治影响力。俾斯麦和拉萨尔都旨在通过这种选举制度削弱自由派的力量。自由主义者充分意识到,新的投票方式一段时间内将削弱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但他们不在意这些。他们认识到,只有全民族共同努力,自由主义才能取得胜利。重要的不是自由主义者占据议院多数席位,而是让自由主义在人民中,从而在军队中也占据多数。在普鲁士下院,进步党人的数量超过了政府的盟友,尽管如此,自由主义依然力量薄弱,因为军中大多数人仍然忠于国王,国王可以信赖他们。愚昧落后的民众的政治冷漠是专制主义的护城河。自由主义者需要将这些人领入自己的行列。只有到那时,才能迎来平民政府和民主的曙光。
因此,自由主义者并不害怕新的选举制度会推迟和严重危及其不可阻挡的最终胜利。从短期来看,未来不是很令人欣慰,但最终的愿景是美好的。只要看看法国就知道了。在那个国家,也有一个独裁者依赖军队的忠诚和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建立了专制统治。但是现在皇帝被击垮了,民主取得了胜利。
自由主义者并不太害怕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可以预计,理智的工人们很快会发现社会主义乌托邦不切实际。工薪阶层生活水平每天都在提高,他们难道会被传言中被俾斯麦收买的煽动者带到沟里去(deluded)?
直到后来,自由主义者才意识到整个民族的心态都在发生变化。多年来,他们认为这只是一次暂时的挫折,一个注定会很快消失的短暂的反动事件。对他们来说,每一位新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要么是被误导了,要么是变节了。但是变节者的人数在增加。年轻人不再加入自由主义的党派。自由主义的老兵们气馁了。每一次新的选举过后,自由主义的队伍都在缩小;他们所憎恨的反动制度,一年比一年强大。一些信念坚定的人仍然坚守自由和民主的思想,英勇地反对左派和右派对自由主义的联合夹击。克尼格雷茨战役后出生的人,几乎没有人加入自由主义政党。自由主义绝种(die out)了。新一代人甚至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前面刚看到有人吐槽很多人权力(Power)和权利(Right)不分,等级社会就是权力导向的,人总是想要决定他人的命运,而自由的社会是多少人自己更关注自身,对自己负责,从而决定自己的命运。
不可行!
人不是工具也不是负担,这种想法仍然是计划经济思维,仍然是等级社会,把低等级的人当作高等级人的手段。
恶龙之所以死而不亡,因为它存在于大多数人的心中。使得秦制延续两千年的,是此地人们普遍的“百代犹行秦法政”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像忒修斯之船一样。
这还是纯自有资金不加杠杆的情况,加了杠杆容错度会非线性骤降,对止损和头寸管理没概念的人很容易忙忙碌碌最终被一波带走。
塔勒布:为了吸引资本,风险更高的投资必须提供更好的收益前景、更高的承诺收益或预期收益,但绝不表示这些更高的预期收益必须实现…在可能导致破产的策略中,收益永远抵消不了破产的风险…脆弱公司的经营杠杆也一样。营业额增加10%带来的利润增加额,低于营业额下降10%带来的利润减少额…如果有一个随机过程,其过往的历史概率不能适用于其未来的情景,那么这个随机过程就不具有遍历性。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系统存在一个类似于“叫停”的机制,这其实就是一个有吸收壁的随机过程,参与这样一个随机过程的“风险共担”就意味着一旦被吸收壁吸收,你就不能回到随机过程中继续游戏了。由于不存在任何可逆性,我们将这种情况称为“爆仓”。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一旦存在“爆仓”的可能性,那么成本收益分析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如今很大的问题在于,很多很多加了高杠杆还死扛的人早已错过了“爆仓点”,几乎就是活死人了。
弥补亏损所需要的盈利幅度
因为,净值是连续的,复利是几何平均数,几何平均数是乘法关系,乘法又具有交换性。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应避免大幅亏损,早或晚都是一样的,马克·斯皮兹纳格尔的“风险缓释”、塔勒布“反脆弱”以及海龟的“生存第一法则”或者“截断亏损让利润奔跑”实际上是一回事。
图中的亏损幅度,换算成(1-亏损幅度)的形式,就比较容易计算和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