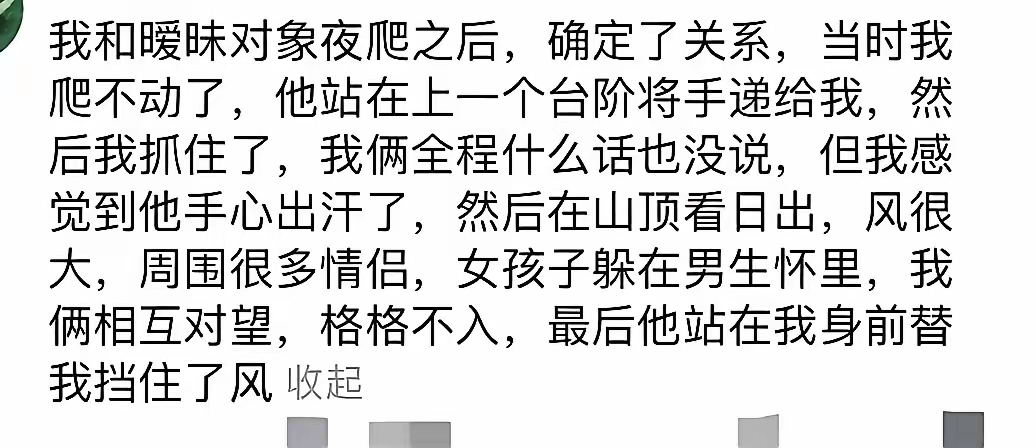大保健前倒是每年洗一次,后来频率降到2-3年了,国内洗牙还是便宜的,小几百够了。我平时家里冲牙器+电动牙刷,公司还扔一把电动牙刷,口袋常备牙线应付外出吃饭,每次洗牙护士都说没洗过这么干净的。
最初的计划是把总资产的1/3换成加密币,现在看来至少应该一半以上,需不需要超过2/3则是等达成了以后再视情况而定。这个政权已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榨干老百姓,再不抛弃法币本位的思维,迟早什么都剩不下。
然而,所有的政府都坚决地不放弃通货膨胀和信贷扩张的政策。他们都把灵魂卖给了宽松货币的魔鬼。能够用花钱的方式来让公民满意,这对每一个政府来说都很舒服,因为公众舆论会把由此而产生的繁荣归功于其当前的统治者。那不可避免的衰退要到后来才会发生,并成为他们的继任者的负担。这是典型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倡导者凯恩斯勋爵说:“长远看来,我们都死了。”但不幸的是,我们都比那个短期活得更长久。我们注定要花几十年的时间来为几年的宽松货币狂欢买单。
—— 米塞斯《全能政府》
#### 古罗马衰败的终极之因
摘自:米塞斯《人的行动》
没有哪个罗马人意识到,这个社会瓦解的过程是政府干预价格和通货贬值所引发的!
浅论古代文明衰落的原因
将罗马帝国的经济组织称为资本主义是否正确,是一个可以搁置不理的问题。无论如何,在罗马帝国(公元)第二世纪,“好”皇帝安东尼治下的社会分工和区域间贸易无疑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好几个大都会中心、为数不少的中型城镇和许多小乡镇,都是某种高度文明的所在地。这些都会区居民的食物和工作材料供给,不仅来自邻近的农业地区,也来自一些遥远的省份。流入都市的粮食和材料供应,有一部分是某些富有都市居民的实物收入,这些人在农村地区拥有田产;但是,也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城市居民用自己加工制成的产品,和农村人民交换产品购买进来的。这个庞大帝国各区域之间存在广泛的贸易。不仅在一些加工制造业,而且在农业,都有进一步专业化的趋势。帝国各个部分,经济上不再是自给自足,而是相互依赖的。
导致罗马帝国衰落和罗马文明腐朽的原因,是这个经济相互关联网的崩溃,而不是野蛮民族的入侵。这些外来侵略者只不过利用帝国内部衰弱所提供的机会罢了。从军事观点来看,在第四五世纪入侵帝国的部落民族,并不会比罗马兵团稍早轻易击败的那些军队更难对付。但是,帝国已经变了!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已经是欧洲中古世纪那种结构了。
罗马帝国准许商业和贸易享有的自由,始终是有限的。在谷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销售方面,商贸自由甚至比其他商品更受限制。在谷类、食用油和葡萄酒等当时大宗消费物资方面,商人索要的价格如果高于通常的水平,会被视为不公平、不道德,而各个市政当局会很快制止所谓不当的牟利行为。因此,这些商品的批发贸易业发展受阻,很没效率。当时所谓的annona(粮食配给)政策,等于把谷类贸易国营化或市营化,旨在填补民营业者的无效率所造成的供需缺口。但是,它的效果却引人反感。一方面,谷类在都会区供给缺稀,而另一方面,农夫则抱怨种植农作物无利可图。当局的干预打乱了供给因应需求上升的调整步骤。
摊牌的时刻于第三世纪和第四世纪到来。当时好几任皇帝为了解决一些麻烦的政治问题,采取通货贬值的办法。在最高价格管制下,通货贬值完全使必要的粮食生产和销售陷入瘫痪,并瓦解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组织。当局愈是认真执行最高价格管制,那些必须购买粮食过活的广大都市民众愈是绝望;谷类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买卖,完全消失不见。为了避免饿死,人们离弃城市,定居在乡村,并且尝试生产谷物、食用油、葡萄酒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自己。另一方面,大规模地产的所有者缩减生产过多的谷物,并且开始在他们的农场住宅——他们的别墅——生产自家需要的一些手工艺产品。因为他们的大规模农场经营模式原本就因为使用无效率的奴隶劳动而严重陷入险境,现在又没机会按有利可图的价格销售产品,于是完全失去维持下去的理由。拥有地产者既不再能在城市里销售他的谷物,也就不再光顾城市里的工匠店铺。他被迫寻找某个替代方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于是就雇用一些手工艺人员,在他的别墅里生产原本从城市里购买的手工艺品。他同时也结束了大规模农场经营,变成一个地主,按时从佃农或承租农收取地租。这些佃农或承租农,若不是释放的奴隶,就是从城市移出的平民他们,定居在乡村地区,重新或起步尝试耕种土地。于是出现一个趋势:每个地主的大规模地产上都倾向于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体系。城市的经济功能,即商业、贸易和城市的手工艺业萎缩;意大利和帝国的一些省份,退回到社会分工发展比较落后的阶段。古代文明高度发展的经济结构,退化成我们现在称为中古时代庄园组织的那种经济结构。
这样的发展逐渐浸蚀并破坏了帝国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对此,罗马帝国的历任皇帝感到惊惶,也采取了对策,但是没有成效,因为没触及问题的症结。他们所采取的强制和胁迫手段,不但未能翻转社会瓦解的趋势,甚至适得其反;因为该趋势正是强制和胁迫太多所导致的。没有哪个罗马人意识到,这个社会瓦解的过程是政府干预价格和通货贬值所引发的!历任皇帝都颁布法令,惩罚“离弃都市到乡村定居(relicta civitate rus habitare maluerit)”的都市居民,结果根本没有用。称作leiturgia的制度——富有的城市公民必须奉献一定的公共服务,只加速了社会分工的解体。还有,私有船主(navicularii)必须承担一些特别责任的法律规定,对于遏止航运业的衰退,比起那些旨在遏止城市农产品供给萎缩的谷物交易法律,成效也没更好。
这个了不起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沦于消亡,原因在于它没有调整道德律和法律体系,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一个社会秩序注定消亡,如果它正常运作所要求的那些行为遭到道德标准排斥,被该国法律宣布为非法,并且遭到法庭和警察机关当作罪犯起诉和拘捕。罗马帝国之所以瓦解、粉碎,只是因为它欠缺自由主义和自由企业的精神!干预主义政策和干预主义在政治上的必然结果——领袖原则——瓦解了这个强大的帝国,正如它们也必然会瓦解和摧毁任何社会实体一般。
经费用完了😇
银行的信用扩张扰乱了那个告诉商人们有多少储蓄可用、多长的项目可以盈利所不可或缺的“信号”——利率。在自由市场中,利率是时间维度上不可或缺的指引,告诉企业家消费者需求的迫切程度。但银行干预市场打破了这一自由价格,使企业家无法正确估计生产最为有利的时间结构。
企业受到信用扩张的引导,去投资更高的阶段,仿佛有了更多储蓄可用。由于储蓄并没有增多,企业在较高阶段投资过度,较低阶段投资不足。一旦消费者有了能力(即一旦新钱进入了他们手中),他们便会抓住时机重建他们的时间偏好,因此也就是重建旧的价差和投资一消费比。在最高阶段投资过度,在较低阶段投资不足,现在也就原形毕露了。
—— 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
昨晚起webtunnel好像又暂时不行了
#### 米塞斯:关于自由的银行业论述的几点意见
《人的行动》第四篇 交换学或市场社会的经济学
第十七章 间接交换
第12节附 关于自由的银行业论述的几点意见
银行学派说,银行如果只做短期放款的业务,便不可能过度发行钞票。当贷款到期偿还时,钞票便从市场上消失,回到银行手中。然而,只有在银行收缩放贷金额时,这事才会发生。(但是,即使这样,它也不会撤销先前扩张信用的效果;只是在该效果之上添加一个后来的信用紧缩效果。)银行通常的作法,是以贴现新商业汇票,取代到期还款的旧商业汇票。于是,对应于旧贷款的偿还、而从市场收回的钞票,银行又重新发行了同等金额的钞票。
在自由的银行业体制下,使信用扩张受限的那个连锁效应,以不同于银行学派所说的方式运作,完全不涉及前述所谓Fullarton原则所想象的过程。它是由这个事实引起的:信用扩张本身不会扩大相关银行的客户群,亦即,把相关银行的即期债务视为货币替代物的人数不会增加。如前所述,当一家银行单方面过度发行信用媒介时,该银行的客户对非客户的支付金额会增加,因此它所发行的货币替代物被非客户要求赎回的数量也会跟着增加。于是,迫使扩张信用的银行重新收缩信用。(Vera C. Smith,在她值得称赞的著作中,The Rationale of Central Banking (London, 1936), pp. 157 ff.,对于这个最根本的事实,没给予适当注意。)
在支票存款方面,这个事实从来没遭到质疑。显然的,一家扩张信用的银行会很快发现,在它和其它银行清算时,已遇到了困难。然而,人们有时候认为,在银行发行的钞票方面,情况是不同的。
交换学在处理货币替代物问题时,主张:货币替代物被某一数目的人们当作货币处理,亦即,它们像货币那样,被某些人在交易中付出和接受,也被某些人保持在现金握存中。关于货币替代物,交换学所说的一切,都预设这个情况。但是,我们决不可荒谬地认为,任何银行所发行的每一张钞票都实际成为货币替代物。发行银行必须享有特殊商誉,才能使一张钞票变成一个货币替代物。人们对于银行在任何时候立即、免费对持有者赎回每一张钞票的能力或意愿,只要有丝毫的疑虑,这个特殊商誉就会遭到伤害,从而该家银行所发行的每一张钞票就会失去货币替代物的性质。我们可以假设,每个人不仅愿意得到这种有问题的钞票作为借款,而且也宁可收取它们作为当下接受偿付的手段、也不愿再多等待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关于它们的主要性质存在任何疑虑,人们将会急忙把它们用掉。人们将在现金握存中,只保持货币,和他们认为绝对安全的货币替代物,而把那些可疑的钞票尽快处理掉。这些钞票将会被折价交易,而这个事实将使它们迅速涌回发钞银行,因为只有该家银行必须按面值全额赎回它们。
回顾欧洲大陆的银行业发展情况,可以把这里的问题说得更为明白。在欧洲大陆,对于商业银行创造支票存款的金额,并没有任何法律限制。它们按理能够采取英美语系国家里的银行所使用的那些方法,发放循环信用、从而扩张信用。然而,一般民众并不准备把这种银行存款当作货币替代物处理。一个收到支票的人,通常立即把它兑现,从银行领走票面金额的货币或货币替代物。所以,对一家商业银行来说,除非金额微不足道,否则不可能以贷记借款人账户的方式发放任何贷款。因为一旦借款人开出支票,银行就会被提领该张支票面额的货币。只有一小群大企业把存放在它们国家中央发钞银行的存款(注意:不是存放在商业银行的存款),当作货币替代物处理。虽然大多数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存款业务方面,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它们却不敢使用存款作为大规模信用扩张的载具,因为会把存款货币当作货币替代物的客户人数太少了。银行钞票实际上是循环信用和信用扩张的唯一载具。类似的情况,过去存在于世界上所有不采用英美语系银行业务方法的国家,现在大体上也大多存在。
在十九世纪八〇年代,奥地利政府推行一个计划,在邮政储金汇业局设立一个支票存户部门,藉以普及化支票簿货币。这计划在某一程度内算是成功。把邮局这个部门的账户余额视为货币替代物的客户群,比该国中央发钞银行支票存款部的客户群还更为广泛。这套制度后来被一九一八年继承Habsburg帝国的新奥地利联邦保存下来;也被许多其它欧洲国家实行,例如:德国。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存款货币,纯粹是政府的一项业务,而这套制度授予的循环信用也完全贷予政府。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奥地利邮政储金机构的名称,不是储蓄银行,而是储蓄局(Amt),而国外的模仿者大部分也都使用这个名称。在大部分非英美语系国家,除了政府邮政系统的这些活期存款,银行钞票是循环信用的唯一载具。(政府控制的中央发钞银行的存款,在某一很小的程度内,也是循环信用的载具。)在讲到这些国家的信用扩张时,我们几乎完全在说银行钞票的增加发行。
在美国,许多雇主以开立支票的方式,支付薪水、甚至工资。只要这些受款人立即兑现收到的支票,并且把全部金额从银行提领出来,这种支付薪资的方法,只意味摆布钱币和钞票的繁重负担,从雇主的出纳身上移转到银行的出纳身上。它没有任何交换学上的意义。如果所有人们都这样处理收到的支票,银行存款便不是货币替代物,便不可能用作循环信用的载具。完全是由于实际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民众把银行存款视为货币替代物,才使得银行存款成为普遍称为支票簿货币或存款通货的东西。
把自由银行业概念,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发行钞票、从而都可以自由欺骗民众这样的印象,联想在一起,是一个错误。人们时常提到曾被Tooke(译者注:Thomas Tooke (1774-1858),英国经济学家,银行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引用过的一句出自某一不知名的美国人的警语:“自由的银行业,就是自由的坑蒙、拐骗。”然而,在银行可自由发行钞票下,银行钞票的使用习惯,即使没被彻底扑灭,也将大幅缩小。一八六五年十月二十四日Cernuschi在法国银行法审查听证会上提出的,正是这个想法:“我相信,所谓自由银行业的体制,将导致钞票在法国完全遭到扑灭。我希望赋予每个人发行钞票的权利,以便不会再有任何人接受任何钞票。”(参考Crenuschi, Contre le billet de banque (Paris, 1866), p. 55。)
有人可能坚持这样的意见:钞票比钱币更便利好使,因此基于方便的考虑,人们乐于使用钞票。如果情况真是这样,人们将愿意支付额外费用,以避免他们装满一口袋沉重钱币所造成的不便。因此,在早期,偿付能力毫无问题的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交换价值稍微高于金属货币。也因为如此,旅行支票相当受欢迎,尽管发行旅行支票的银行要收取一定的发行手续费。但是,这个事实和这里讨论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它不是可以用来为各种促使民众使用钞票的政策辩护的理由。各国政府不是为了让逛街采购的女士免于不便、而促使人们使用钞票。各国政府的主意,是要降低利率,是要给它们的财政部打开一个低利贷款的来源。在它们看来,增加信用媒介数量,是增进国民福祉的一个手段。
各种钞票并非不可或缺,即使它们未曾存在过,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成就还是一样会达成。此外,存款货币做得到所有钞票能够做到的事情。而且,要为政府对商业银行存款业务的干预作辩护,也不可能引用“保护贫穷无知的工薪阶级和农夫,免于邪恶的银行家伤害”这个伪善的借口。
但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多家商业银行组成一个卡特尔,那会怎么样呢?难道各家银行不可能勾结起来,以便无止境地扩大发行它们的信用媒介?这个反对自由银行业的理由,是荒谬的。只要一般民众没因政府干预、而丧失从银行提领存款的权利,便没有哪一家银行能够冒自毁商誉的风险,和一些商誉不如自己响亮的银行勾结在一起。我们决不可忘记,每一家发行信用媒介的银行都处在一个相当不确定的危险位置。它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它的信誉。一旦产生任何关于它是否完全值得信赖、是否有偿付能力的疑虑,它必定破产倒闭。对一家信誉良好的银行来说,把它的招牌和商誉比较差的其它银行招牌连结在一起,无异于自杀。在银行业自由体制下,银行卡特尔将摧毁国家整个银行体系,对任何银行都没有好处。
信誉优良的银行大多因为保守经营和不愿意扩张信用而遭到指责。在那些不值得银行授信的人们看来,限制信用扩张,显然是一种恶行。但是,在银行业自由体制下,限制信用扩张却是银行经营首要和最高的准则。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要想象自由银行业的情况,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因为他们把政府干预视为理所当然和必要的一回事。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政府干预银行业,是以一个错误的假设为根据的;它误以为,信用扩张是永久降低利率的一个适当手段,除了麻木不仁的资本家,不会伤害任何人。各国政府所以干预银行,恰恰因为它们知道,自由银行业会把信用扩张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
有些经济学家断言,就银行业目前的状况来说,政府对银行业的干预是合理的;他们这个说法,也许是对的。但是,银行业目前的状况,不是未受干扰的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它是各种政府措施,企图实现大规模信用扩张所需条件,造成的结果。如果政府从未干预,银行钞票和存款货币的使用,将仅限于对分辨银行有无偿付能力知之甚详的那些阶层人士。大规模的信用扩张将不可能发生。现在,普通人怀着迷信的敬畏,看待每一张被国库或国库所控制的机构印上法币这两个魔术字眼的纸;这种迷信的四处散布,是政府一手造成的。
政府对目前的银行业经营状况进行干预,如果目的是要阻止或至少严格限制进一步的信用扩张,藉以清除不好的银行业情况,那么是值得辩护的。然而,事实上,当今政府干预的主要目的,却是要加剧进一步的信用扩张!这个政策注定会失败;迟早一定会造成大灾难。
#### 民族自决权与公民自决权
(摘自:米塞斯《全能政府》,可二译本)
自由主义的敌人努力证否(disprove)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民主政府的价值的义理,他们失败了。那么,在批评自由主义纲领的第三部分——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实现和平协作的意见——时,他们是否更加成功?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再次强调,民族-国家化原则并不是自由主义用以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自由主义者竭力主张自决。民族-国家化原则是中欧和东欧民族解释自决原则的产物,后者从未充分领会自由主义观念的含义。民族-国家化原则是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歪曲,而非完善。
我们已经表明,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兰西自由主义观念的先驱们并不了解这些问题。当这些问题凸显时,传统自由主义的创造性时代已经落幕。伟大的领军者已不在人世。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站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没有能力成功击败日益滋长的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风潮。这些人缺乏处理新问题的力量。
然而,老派古典自由主义回光返照的小阳春(Indian summer)时代,却产生了一份配得上法国自由主义伟大传统的文献。诚然,欧内斯特·勒内(Ernest Renan)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社会主义面前,他有所让步,因为他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相当贫乏;因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民主偏见太过宽容。但是,他的著名演讲《什么是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深受自由主义思想之启发。1882年3月11日,勒内在索邦大学发表了这番演讲。这是西方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国家和民族问题上的最新成果(the last word)。
为了正确理解勒内的思想,有必要记住,对于法国人和英国人而言,“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是同义词。当勒内问:什么是民族(nation)?他的意思是:应该由什么决定各个国家(state)的边界?他回答道:不是语言共同体,不是建立在共同祖先之血统基础上的种族亲缘关系,不是宗教上的意气相投,不是一致的经济利益,不是地理或战略考量,而是——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民族是希望同处一国生活的人类之意愿的产物。勒内的讲座用来更大的篇幅来展示这样一种民族-国家化精神是如何产生的。
民族是一种灵魂,一种道德原则(“une–me,un principe spirituel”)。勒内说,通过不断表明其在同一个国家内进行政治合作的意愿,一个民族日复一日地确定其存在;就像是公民日复一日地投票决定其存在。因此,一个民族无权对一个地区说:你属于我,我要带你走。地区由其居民组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谁有权发声,那就是这些居民。边界争端应该通过公民投票解决。
对自决权的这种解释与民族-国家化原则的解释有很大区别,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勒内心目中的自决权不是语言族群的权利而是个人的权利。它源于人的权利。“人既不从属于他的语言,也非从属于他的种族,人属于他自己”。
从民族-国家化原则的观点看,存在像瑞士这样由不同语言的人组成的国家,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西人并不急于将所有讲自己语言的人统一到一个国家中一样,都是反常的现象。但对勒内来说,这些事没什么不合常规。
与勒内说出来的话相比,他没有说的话更值得注意。勒内没有看到语言少数族群(linguistic minorities)问题和语言变迁问题。征询人民的意见;让他们决定。一切都妥当了。但是,如果明显的少数派反对多数人的意愿呢?对于这一异议,勒内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他宣称,公民投票可能导致传统民族的解体和小国体系(如今天我们说的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由于这一顾虑存在,自决原则不应滥用,而只能以一般方式(a general way)使用(d’une façon très générale)。
勒内的精彩论述证明,对那些在东欧造成威胁的问题,西欧并不熟悉。勒内以一个预言为他的一本小册子作序:我们正冲进那些破坏与毁灭之战,因为世界已经放弃了自由联合原则,并像它曾经赋予各王朝一样,赋予各民族兼并那些反对兼并的区域之权利。但是,勒内只看到了问题的一半,因此,其解决之道也只能是半途而止。
然而,如果说自由主义无法解决这一领域的问题,那就错了。自由主义关于民族与国家共存合作的提议只是自由主义全部纲领之一部分。自由主义者能意识到,这些提议只能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起作用。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自由化计划的主要优点,正在于它使民族间的和平协作成为可能。在反自由主义的世界里,自由主义的国际和平纲领无法实现;在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自由主义的国际和平纲领必然失败。这并非该纲领的缺陷。
为了领会这一纲领的含义,我们需要设想一个自由主义至上的世界秩序。在这个世界秩序中,要么所有国家都已经自由化了,要么当自由国家联手时足以击退军国主义侵略者的侵犯。在这个自由的世界,或者说这个世界已自由化的那部分地方,生产资料属于私人所有。市场的运作不受政府干预的阻碍。不存在贸易壁垒;人们能如其所愿选择生活和工作地点。地图上划定了国界,但是边界并不妨碍人的迁徙和商品流通。拒绝给予外人的那些权利,本地人也同样不能享有。政府及其雇员的行动严格限制在保护生命、健康和私有财产免受欺诈或暴力之侵犯的范围之内。政府不歧视外国人。法院是独立的,有效保护每个人不受官僚的侵犯。每个人都允许表达、写作和出版那些他喜欢的东西。教育不受政府干预。政府就像守夜人,公民托付政府掌控警力。官员被视为凡人,而非超人或有权利和义务监控人民的父母般的权威。政府无权命令公民在日常讲话中必须使用什么语言,和以什么语言养育子女。如果当地有相当数量的居民讲某种语言,行政机关和法庭必须使用这种语言与每个人打交道。
在这样的世界中,国家的边界划在哪里不会有区别。扩大自己所在国的领土,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特殊的物质利益;自己所在地从国家中分离出去,也不会有人蒙受损失。国家领土的所有组成部分是否存在直接的地理联系,或者是否被属于他国的领土隔开,也无关紧要。该国是否拥有临海的海岸线,在经济上并不重要。在这样的世界中,每个村镇或地区的人民都可以通过公民投票如其所愿决定它们归属哪个国家。不会再有战争,因为不存在激励侵略的动机。战争不会有回报。陆海军是多余的。警察足以打击犯罪。在这样的世界,国家不是什么玄奥的东西,它只繁育安全与和平。它正是如拉萨尔所蔑称的“守夜人”,但是,它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完成了这项任务。国家不会将公民从睡梦中惊醒,炸弹不会落在公民的屋顶。如果有人深夜敲门,此君也必非盖世太保或者格别乌(O.G.P.U)。
我们不得不身处其间的现实,与理想自由主义的完美世界大不相同。但这只能归咎于人们因为国家控制主义而拒绝自由主义。政府本来或多或少是有效的守夜人,但是人们让政府担负了许多其他职责。并非是自然、或者某些不受人类控制的力量之作用、或者某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而是人们的行动导致了国家控制主义。人们深陷辩证法的谬误和狂热的幻觉,盲目相信错讹的学说,被嫉妒和无法餍足的贪婪带偏了,他们嘲讽资本主义,而以一种正在持续引发冲突的秩序取代资本主义体系,这种秩序无法找到和平解决之道。
注:
可二先生的译本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尚未出版,如需电子版可添加公众号“可二碎碎念”向他索取。可二的译本添加了海量的译者注释;对米塞斯知识广度和深度稍有了解的读者应该很清楚,这样数量庞大的注解意味着什么。
一定要让牢柏杏牢役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