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當年黑鷹墜落,摔死一個將軍、八個大校的時候,新華社可是連個屁都沒敢放。
其實中國人是在進化的。臘肉太祖死的時候,有95%的中國人會真心實意的痛苦流涕,哪怕是那些被它害得生不如死的人;現如今雖然是竹幕重啟、鐵腕禁錮,哪一天慶豐帝溺斃在尿桶裡,最少會有30%的中國人至少會在心裡說:“活該!這孫子可算他媽完蛋了!”
和一個退休的馬自達老工程師聊天,他是最早去中國的一批技術人員,我隨口問為什麼其他日本品牌都是直接在中國用自己的漢字,而馬自達選擇了音譯?他說不行啊,直接用漢字就壞了,然後我一下就明白了……
(まつだ=松田) https://t.co/5dSzMwDrOq 
只要腦袋不肯,那麼無論屁股或嘴巴都不會說出違心的話。打賭你們不知道出處。
今年的淺草三社祭雖然警方明令禁止黑社會展示紋身,還是攔不住,和警方還發生了衝突。 https://t.co/KEO8Zgz0o9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_video/1792375795736100864/pu/vid/avc1/1024x576/ujuqDhslTOdk98Cl.mp4?tag=12
對於這世界上的使用TIKTOK的未成年人來說,如果錄一段視頻能達到100萬贊,殺掉親生父母也不會猶豫。
應該是好了…… https://t.co/Lst70Se2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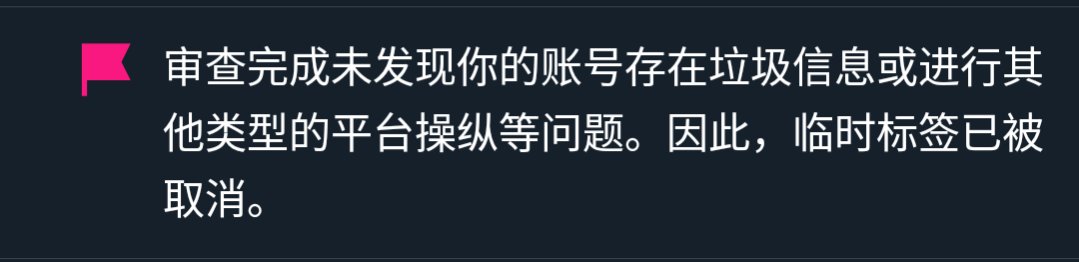
莫名其妙,寫的東西都丟了,關注也變成0了。 https://t.co/O0MLA0WZX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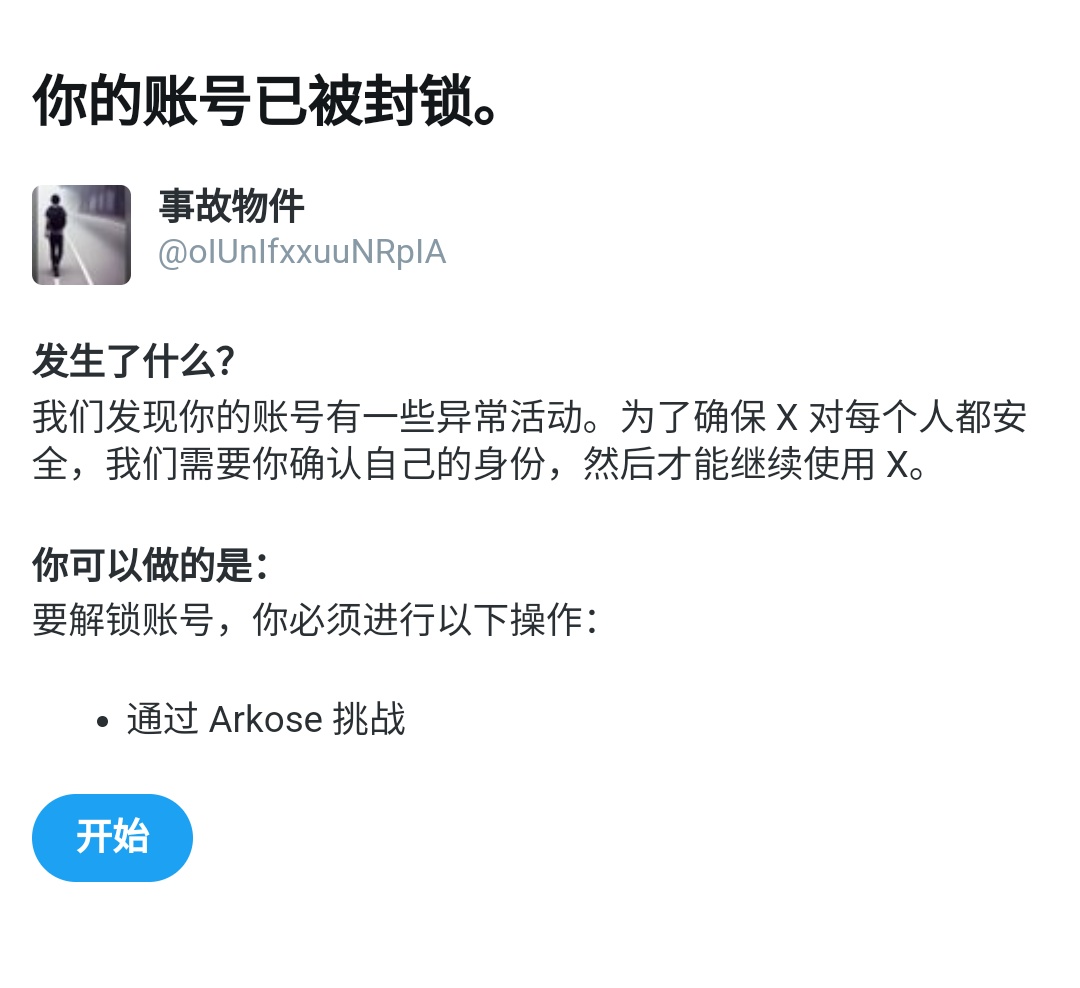
原來我一直把梁詠琪唱的《膽小鬼》中的“叫我膽小鬼”,聽成了“叫我當小烏龜”。
「如今世界上的老實人不多了,米勒太太。 我想斐迪南大公在薩拉熱窩也準是把那個槍殺他的人看錯了。 他準是看到那人對他滿口甜言蜜語,就以為這是個好人,結果反讓這位老兄把他幹掉了。 他們朝他身上開了一槍還是幾槍? 」
「報上說,先生,大公的身子給打得淨是篩子眼兒。 刺客把子彈全打光了。 」
「幹得真痛快,乾淨俐索,米勒太太。 要是我去幹那號子事兒,就得買支勃郎寧。 這種手槍看起來像個玩具,可是只消兩分鐘,就可以連胖子帶瘦子打死他二十個大公。」
(事故物件的鬼故事:野原之四)(#事故物件的瞎扯)我們退開幾步,一個模糊的黑影從火堆中慢慢站了起來,依稀可以看出是個人形,但能看清的只有一張臉。他伸了個懶腰,在周身上下拍打著,似乎要清理身上的塵土,完事自己搬了一塊大石頭,也坐在火邊,然後招呼我們回去坐。“謝謝幾位啊,在我這一把老骨頭上生了火,好久沒這麼暖和了!”沒人搭話,大家還是攥著傢伙,做著隨時開打的準備。他自顧自地撿起塌子掉在地上的煙,深吸了一口,轉頭看我:“你是頭兒吧?沒事,甭怕,你們不是惡人,我們也不是惡鬼。按說你們根本不該怕我,我是革命老前輩啊,紅軍。給你們開創美好生活的老紅軍,你們上學的時候就沒在作文裡歌頌過我?”說到這兒,他自己應該是覺得很有意思,自顧自地笑了起來。我看清了那是一張四五十歲的臉孔。
影子還在抽煙,貪婪地深吸著,香煙的火頭隨著一亮一暗,可是香煙並沒有變短。等他停下來,把手裡的煙向旁邊遞出去,又有個黑影出現,默默地抽上幾口,再遞出去。我們四個人退到一起,背靠著背,看著周圍一個又一個,一片又一片的黑影起身,慢慢覆蓋了整個視力所及的原野。我們掉在地上的煙都被撿了起來,在黑影們當中一亮一滅的傳遞,慢慢地向原野的遠方走。北風在吹,並不太強,所以我們能清晰地聽到虞頭兒牙齒打戰的咳咳聲,我們另外三個人對視了一眼,塌子一把把虞頭兒拉進了最中間。
自稱紅軍的黑影轉頭看了我們一圈,又笑了。“四位都跟著家神,還有兩位帶印的,你瞧這孩子今兒晚上這簍子捅的。”(注:我和武子山神一仗後留下的傷疤,後來家神才告訴我,那是山神的結印,沒什麼傷天害理的劣跡就不會褪,精靈魍魎害不了我們。)這話聽起來並不兇惡,看我們不動,他轉過頭去,伸手烤火。那四根煙還在黑影們當中傳遞,星空下到處都有縷縷煙霧升騰著,偶爾這裡或哪裡會有人說話,聽不懂的語言,大概意思應該是給我也抽一口吧之類。
停了一會兒,我覺得這麼僵著不是事兒,人家笑瞇瞇地以禮來,我們橫著傢伙繃在這兒,又冷又沒用,就招呼大家回到火邊坐下。火堆邊上的黑影們閃出了我們原來坐的石頭位置,我和武子一左一右夾著自稱紅軍的影子坐下,塌子本來想奔武子的位置去,被武子一把推開:“你沒經過這個,護著虞頭兒吧!”我試著搭話:“這兒是您貴處啊?我們這兄弟夜裡開得快,多有衝撞,請問怎麼稱呼?”這下影子笑出了聲:“我們是鬼,哪兒來的什麼貴處。甭怕,只是那孩子想要學開車,這邊夜裡車少,趕上你們了,多有得罪,他不是要害人。”說到這兒,他站起來招招手,一瞬間遠處飄搖的白影就到跟前,一個十六七歲少年靦腆的臉,只是發式不常見,中間剃光,兩邊鬢角垂著發辮。
我們走過的少數民族地區不少,卻沒見過這種,我看了塌子一眼,他喃喃地冒出一句:“藏族吧?”沒什麼自信。紅軍又笑了,挺大的聲音。他和附近的黑影嘀咕了幾句,就有一片笑聲響起。鬼魂們之間好像語言並不通用,要不斷的互相翻譯著才能聽懂,不斷有一些影子出來說上兩三句,笑聲像一個擊鼓傳花的遊戲,在原野上越傳越遠,越來越大聲。
笑夠了,紅軍伸手拉過白影,比劃著讓他張開嘴給我們看,他沒有舌頭。“看明白啦?他是個韃子,匈奴,始皇帝的護靈素軍,都是抓得匈奴崽子,割了舌頭,不認字,專門往皇陵裡搬東西的,洩不了密。”說到這兒,他嘆了口氣,白影子也在火邊坐下來,靠在紅軍身上。“始皇陵?那還離這兒遠著呢?”虞頭兒似乎是忘了害怕,冒出來一句。白影子明顯是聽不懂虞頭兒的話,拉了拉紅軍,一臉疑惑。紅軍伸手摸著他的禿腦勺,又嘆了一口氣。我摸出煙又點著一根遞過去,他說著不用了,卻還是接下來,抽了一口,交給了白影子:“天下大亂,秦軍要殺他們,楚軍也要殺他們,他們幾百人從陝西殺出來,往北走,想回匈奴,走到這兒被追上了。”白影子拿著煙,似乎是覺得很好玩,把有火的一頭放在嘴裡,笑著站起來,給周圍的影子們看,又有一片笑聲在暗夜裡響了開來。
(未完待續)
(事故物件的鬼故事:野原之三)(#事故物件的瞎扯)我和塌子在後車廂被顛了個七葷八素,好容易從羊肉、魚和蘿蔔堆裡爬出來,只聽見駕駛室裡打得正熱鬧。“媽的!虞頭兒怎麼和武子幹起來了?”正納著悶兒,車熄了火,又竄出幾十米停住,只聽見虞頭兒一聲大叫:“小子!你打我幹嘛?”我掀開身上的羊,拍著駕駛樓子問怎麼回事,武子沒多餘的話,只喊了一嗓子:“抄傢伙!”我和塌子雖然不知道緣由,馬上開始翻找。“劫道的吧?”我嘀咕著。“不對!”塌子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不是善茬兒!”“怎麼?”他指了指脖子後面,“我們家祖宗來了!”與此同時,我感覺到家神的手按在了我後腦勺上。
跳下車,武子和虞頭兒也下來了,武子手裡橫著搖車的搖把兒,把虞頭兒護在身後,虞頭兒臉上開了近十公分的口子,滴答著血。“不知道什麼玩意兒,附在虞頭兒身上,讓我一嘴巴給抽出去了。”武子攥著搖把盯著夜色,並沒有回頭看我們。虞頭兒算是明白過味兒來了,開了自己的廚具箱,拎出來一把剁骨刀:“淨他媽聽你們講古了,今兒也讓我趕上一回。”
我和塌子向著武子戒備的方向張望,什麼也看不到。“人沒事,走咱們的吧?”塌子冒出一句,“不行啊!這塊兒都是大石頭,剛才衝過來不知道車傷了沒有,萬一磕漏了油底殼就毀了。”武子還是沒有回頭。我爬上車,熄了大燈,等眼睛適應了,能看見不遠處有個白色的影子隨著風晃來晃去。“要不咱們過去?”虞頭兒的聲音有點哆嗦,雙手緊緊攥著他的寶刀。我想聽一下家神的意見,他給了五個字:“不動,等天明。”我看了手錶,11點半,離天亮還有六七個小時。
冬夜的北方原野寒風刺骨,我們下來得匆忙都沒穿大衣,十幾分鐘就有點堅持不住了。“我說,咱遠日無冤、近日無仇的,有什麼話挑明了說吧!”塌子用手裡的錘子砸著面前的石頭,朝遠處喊,沒有回音。“虞頭兒,您上車把大夥衣服抱下來,武子!甭盯著了,生火。”武子沒打錛兒,撂下搖把開始划拉附近的枯枝爛葉,我用手裡的鐵鍬開始挖坑,塌子開始把附近大小合適的石頭往過搬,虞頭兒有點猶豫,停在那兒沒動。“我說,您老快著點兒嘿,工夫大了,咱們凍也凍死在這兒了!”塌子推了虞頭兒一把,老頭兒張了張嘴,想說什麼又沒說出來。“甭怕,有他媽什麼啊,剛才不就是武子一大嘴巴把丫制了嗎?有事兒,讓武子再給您來一個……”話沒說完,塌子自己就樂上了。虞頭兒又停了幾秒鐘,把手裡的刀遞給塌子,“那什麼,你給叔拿著,有事使勁招呼,叔不怪你。”
火著了,在空曠的荒野裡劈啪的響著。武子還是拿著搖把盯著白影的方向,也被塌子拉著坐在了火堆邊,“離天亮還早,你這麼繃著,撐不了多會兒。”虞頭兒平安無事的把大夥的衣服抱下車,明顯膽氣壯了不少,沒等別人說,又爬上去一趟,翻出來半條煙。“點上,點上!唉,人是鐵,煙是鋼!唉!”四個人都點著了煙,塌子面朝白影坐著,武子得空給我們講了一遍來龍去脈。塌子沒回頭,但是武子說一句,他得評一句,等武子說到用拿車鑰匙的手把虞頭兒體內的白影抽出來,塌子樂開了:“真的假的啊?明兒天亮了我得看看虞頭兒臉上你那指紋清楚不清楚。”“真的!真的!俺擔保是真的。”一個陌生的口音在我們中間響起來,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攥著傢伙跳起來。“別慌,別慌,甭怕,俺們不害人。”一張笑瞇瞇的臉孔從火堆中的石頭上浮現出來,“也給俺抽一口吧!”
(未完待續)
(事故物件的鬼故事:野原之二)(#事故物件的瞎扯)四個人圍著地圖一頓瞎指,虞頭兒的職業敏感讓他每提到一個地名都能帶出來一堆好吃的。塌子最先反對:“這不行啊!咱們繞出來幾百公里問題倒是不大,您可倒好,從肘子到火腿,還得金華的,我不攔著點兒,您這眼看著就要奔宣威下去了,咱這是回家順路,不是周遊列國啊!”一句話,說得虞頭兒洩了氣,但還是堅持著最少要奔銅川下去拐個彎兒:“那兒有黃河鯉魚啊!黃河鯉魚啊!”塌子還是反對,他主張先瞄準肘子,魚的問題最後穿白洋淀去解決。“河北咱有人啊!李隊又升了好像,幾條魚不就是嘛!”
我們把地圖在中部幾個省裡,有熟人或者可能有半熟人的地方標了點,武子把“某某工程指揮部”條幅掛在了車幫上,專門找當地路局門口的飯館,蹲在門口吃面。這招兒果然奏效,沒進陝西就被塌子的大學同學薅住了。相比塌子的駐點工程師,人家已經是路局副局長。“把面撂下、撂下!媽了屄的,到我這兒,不來找我!就吃這個面!這他媽存心丟俺的人唻!”沒多會兒,地方上的頭面官員來了一批,“這是咱大學同學,一局的,公路口最牛屄的!”京裡有人,對地方官員來說,這是天大的面子。一頓大喝,我和塌子撐著沒倒,贏得了一片讚譽。滿桌的官員差不多當場要和我們結拜,人武部長張羅著讓我們多住兩天,開車出去打黃羊。虞頭兒聽見黃羊,眼睛都直了,撂下筷子就要站起來,被沒喝酒的武子一把按住。
臨了,我們說無以為報,車上帶了幾隻羊,留下點兒,給局長添個年菜。這話當然純屬客套,局長的氣兒要從鼻子裡橫著出來。“啥羊?咦!啥羊能比得上咱這兒灘羊,那個誰誰誰,你出去看看,咦!我還就不信了,某某局那些球玩意兒,能變出啥好羊來!”局長手下出去回來,臉上滿是不屑,和局長一樣把臨省的路局罵得一文不值。塌子解釋我們出來七八個人,正好一人半只,人家也是好心。這話沒說完,就被局長揮手摀住了,“你個沒出息的樣子,一人半只,他們也他媽說得出來!你們這,我們請都請不到,在他媽那邊兒給他們辦工程,一人半只?咋了?西北人不要臉啊?”同桌的官員一片喝彩,局長更加高興:“那個誰誰誰,你現在去辦,把他們那羊給我卸了,一人一隻,媽了個屄的!半只,丟人!”說完了,又拉著塌子,“怎麼著,聽說這幾年你把京局的橋說趴下好幾座?是真的嗎?”
再上路,車上換了洗乾剝淨的灘羊和整筐的黃河鯉魚,鯉魚倒不是局長發話,是虞頭兒裝模作樣跟辦事人假裝無意中說起我們還要進陝西,那邊的局給我們備了黃河鯉魚。“咦!那黃河又不是他陝西家的,俺們這兒的魚不比他陝西好!”有什麼官就有什麼兵,這話一點兒不假。沒人再提肘子了,一家一隻灘羊,這年得過得最少是個副局級標準,這是塌子原話。
年底下,局長沒有強留我們多住幾天,只是說好明年他這兒的工程我們必須得帶隊過來。“你們那兩個洋人還在隊上沒有,一起來啊!必須給我一起來!”我們解釋漢斯和荒木君合同到期,已經不在隊上了。局長又拍了桌子:“咱沒這個命啊!見不著高人!那咱可定下了,你們得來,得給我帶出點人來,媽了個屄的,我這沒能幹的,淨一堆粑粑!”
武子開車,跟他這名字差不多,一向是速度貼著輪胎極限。東西齊了,大家歸心似箭。我和塌子在車廂裡羊肉、蘿蔔和鯉魚中間擠出塊地方倒頭睡去。虞頭兒在副駕駛負責給武子點煙倒水。天氣不錯,荒原的夜色也能看出很遠,武子沒走國道,縷著工程圖專找沒車好開的路,一路奔東。虞頭兒點煙相當講究,點上,唑著了,手從方向盤的方向過來,不擋武子視線,直接把煙給他塞嘴裡。
停車撒尿的時候,我問武子要不要換他,“你們挺屍睡你們的,甭跟機械手搶開車的活兒!”這小兔崽子毫不客氣。在車底下一起抽了一根,大家公議這次塌子功勞最大,得多分一份羊下水。塌子眼睛笑得瞇成一條線,一個勁兒地要學虞頭兒獨家的調料秘方。再上車,武子一腳油門,差點踹進油箱。我和塌子在車廂裡罵開了街:“你他媽就不能等我們躺下啊!”回應我們的是武子和虞頭兒的哈哈大笑。
笑聲沒落,一團白影慢慢從路中間升起來,武子急剎,車還沒站住白影已經撲到車前。“媽也!撞人啦!”虞頭兒剛來得及喊出這幾個字,白影已經穿過風擋,直衝進駕駛室,壓在武子身上,往武子衣服裡鑽。武子一手把住方向盤,一手揮開,一個大耳切子把白影抽到一邊。這一巴掌打愣了白影,它似乎是停了那麼瞬間,轉頭把目標對準了虞頭兒,毫無抵抗地撲進了虞頭兒的身體,虞頭兒有了一張蒼白猙獰的臉,一腳跺在油門上,然後撲過來開始搶武子的方向盤。“叔!你他媽幹嘛?”武子吼叫著跟虞頭兒撕扯,車子衝出路基,在荒灘上顛簸。“我肏他媽的!”武子罵出這一句,直接拔了車鑰匙,然後騰出手來,給虞頭兒也來了個大嘴巴!
(未完待續)
(事故物件的鬼故事:野原)(#事故物件的瞎扯)“我一看,好傢伙!他們幾個都讓人放躺下了,就剩我一人兒啦!”德慶說到這兒,停下來,看著周圍的民工。大家伸著脖子等著聽他的下文,德慶賣開了關子,“就這功夫嗨,那周圍山神的兵就跟炸了窩的馬蜂似的,往我這邊衝,得有好幾十,不對,好幾百,也不對,我想想啊!最少一千多吧!嗨嗨嗨,別光直著脖子傻聽啊,給我找根兒煙去,唉!你們在家聽說書,不得給先生掏點兒錢啊?快點兒,快點兒啊!我跟你們說,這煙接不上,我這真人真事兒可也轉眼就忘啊!”急著聽下文的工人們手忙腳亂地翻兜,年關下大家都準備回家了,沒什麼存貨。有人跑到另一堆人裡,蚊子、小武兒和小木兒身邊都圍著一堆人說自己的英雄事蹟,不外乎是別人都廢了,就自己在孤軍奮戰、力挽狂瀾!
小木兒按住面前的煙盒,不讓工人掏煙:“嗨!我說你這,過來連個招呼都不打啊?要煙給誰啊?”民工抓著後腦勺,“德慶師傅沒煙了……俺們也沒了……”“給他?我呸,就屬丫面瓜,第一個讓人放躺下的就是他,乾脆!你也甭走了,坐這兒,聽我給你說說真實情況。就當時嗨,我穿著山神的金甲,那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啊!你就說吧,他們幾個都讓人按在那兒一頓爆捶,那個慘啊!有一個算一個,連隊長在內!”小木兒夾著煙的手畫了一圈,把我也包在其內。“就我身邊兒,誰都不敢過來,我這一邁步哇,就手裡這對擂鼓甕金錘,估計是當年李元霸留下來的,那山神的兵嚇得腿肚子轉筋,我這錘掄起來就是一道金光……”
機械手們歲數都不大,跟山神家裡打了一仗,讓他們憋在肚子裡不說那是萬萬辦不到。不過,神鬼之說,隨便哪個民工肚子裡都能拽上兩段,說得越玄乎,大家也就越愛聽,然後也就越不信,過幾天回了家,跟山神打仗的也就成了他們自己,依舊豪氣幹雲、義薄雲天。
年節將至,工程收了尾,相鄰幾個工段的工人包了火車回家,機械手和工段工程師晚了一兩天。要過年了,和當地路局喝上一頓,弄點雞蛋、紅薯、蘿蔔,甚至幾隻羊,回去幾家一分,媳婦、丈母娘面前有個面子。蚊子帶著德慶、小木兒押著專用機械跟著火車走了,塌子和我帶著武子、虞頭兒開著卡車上了路。“虞頭兒不能單走啊!這快兩千公里了,趕上荒郊野外的,有虞頭兒到哪兒不都得有好吃的。”塌子堅決要拉上虞頭兒,虞頭兒當然願意跟我們一起,公家的車、公家的油,自己能省下火車票錢,還能多帶不少東西。“我說,咱們路上要不要再去幾個局轉轉,這現在雞蛋、蘿蔔、羊肉都有了,要是能再弄點兒魚或者個把肘子,咱這年可就真是不賴了!”虞頭兒有著自己的小算盤。
我和塌子拿著地圖琢磨,魚和肘子從一個地兒扎出來不太可能,也就不能一條直線回家,得多去幾家碰碰運氣,能搞出來東西,大家皆大歡喜,當然不是只有我們車上幾個人的,押車先走的一樣得有,這種事兒非我和塌子這種一肚子花花腸子的辦不了。
(未完待續)
(時間有限,寫一點算一點,沒有日程表)
世界的真相就是:你的擔憂都會變成現實,希望卻不會。
高速公路軟土地施工基準是道橋專業必備的,從現場照片你就可以看到基礎工程是做了還是沒做,到底做了多少。廣東今年降雨多,推到天災就一了百了,沒有天災可推的地方,抓幾個施工單位的人示眾也就息事寧人。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就是這樣,錢沒錢花,去哪兒了?你問了就沒好下場。
被別人火控雷達鎖定後還能吹牛屄,和被人四馬倒攢蹄綁著浸豬籠前大罵:“我肏你媽!”屬於一個性質。該事件充分說明了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遠流長和博大精深,彰顯了臉皮比地皮還厚的民族氣節,體現出中國軍機只要都被對方火控雷達鎖定就注定取得無可辯駁的勝利的大趨勢。
歐亨利的小說《沒有完的故事》節選:
如今人們提到地獄的火焰時,我們不再唉聲嘆氣,把灰塗在自己頭上了。 因為連傳教的牧師也開始告訴我們說,上帝是鐳錠,或是以太,或是某種科學的化合物;因此我們這夥壞人可能遭到的最惡的報應,無非只是個化學反應。 這倒是一個可喜的假設;但是正教所啟示的古老而巨大的恐怖,還有一部分依然存在。
你能海闊天空地信口開河,而不至於遭到駁斥的只有兩種話題。 你可以敘說你夢見的東西;還可以談談從鸚哥那裡聽來的話。 摩非斯和鸚哥都不夠證人資格,別人聽到了你的高談闊論也不敢指摘。 我不在美麗的鸚哥的絮語中尋找素材,而挑了一個毫無根據的夢像作為主題,因為鸚哥說話的範圍比較狹窄;那是我深感抱歉和遺憾的。
我做了一個夢,這個夢同《聖經》考證絕無關係,它只牽涉到那個歷史悠久、值得敬畏、令人悲嘆的末日審判問題。
加百列攤出了他的王牌;我們之中無法跟進的人只得被提去受審。 我看到一邊是些穿著莊嚴的黑袍,反扣著硬領的職業保人,但是他們自己的職權似乎出了一些問題,所以他們不像是保得了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的樣子 。
一個包探──也就是充當警察的天使──向我飛過來,挾了我的左臂就走。 附近候審的是一群看起來境況極佳的鬼靈。
「你是那一撥人裡面的嗎?」警察問。
「他們是誰呀?」我反問說。
「嘿,」他說,「他們是──」
這些題外的閒話已經佔去正文應有的篇幅,我暫且不談它了。
(中間略)
—— 我在前面說過,我夢見自己站在一群境況很好的鬼靈旁邊,一個警察挾著我的胳膊,問我是不是同那群人一起的。
「他們是誰呀?」我問。
「唷,」他說,「他們是那種僱用女工,每週給她們五六塊錢維持生活的老闆。你是那群人裡面的嗎?」
「對天起誓,我絕對不是。」我說 ,「我的罪孽沒有那麼重,我只不過放火燒了一所孤兒院,為了少許錢財謀害了一瞎子的性命。」
